来塔加,做个“诗中人”——读马文秀《老街口》有感
2025-04-23 14:38:34 作者:冶玉丹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冶玉丹,青海化隆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化隆县文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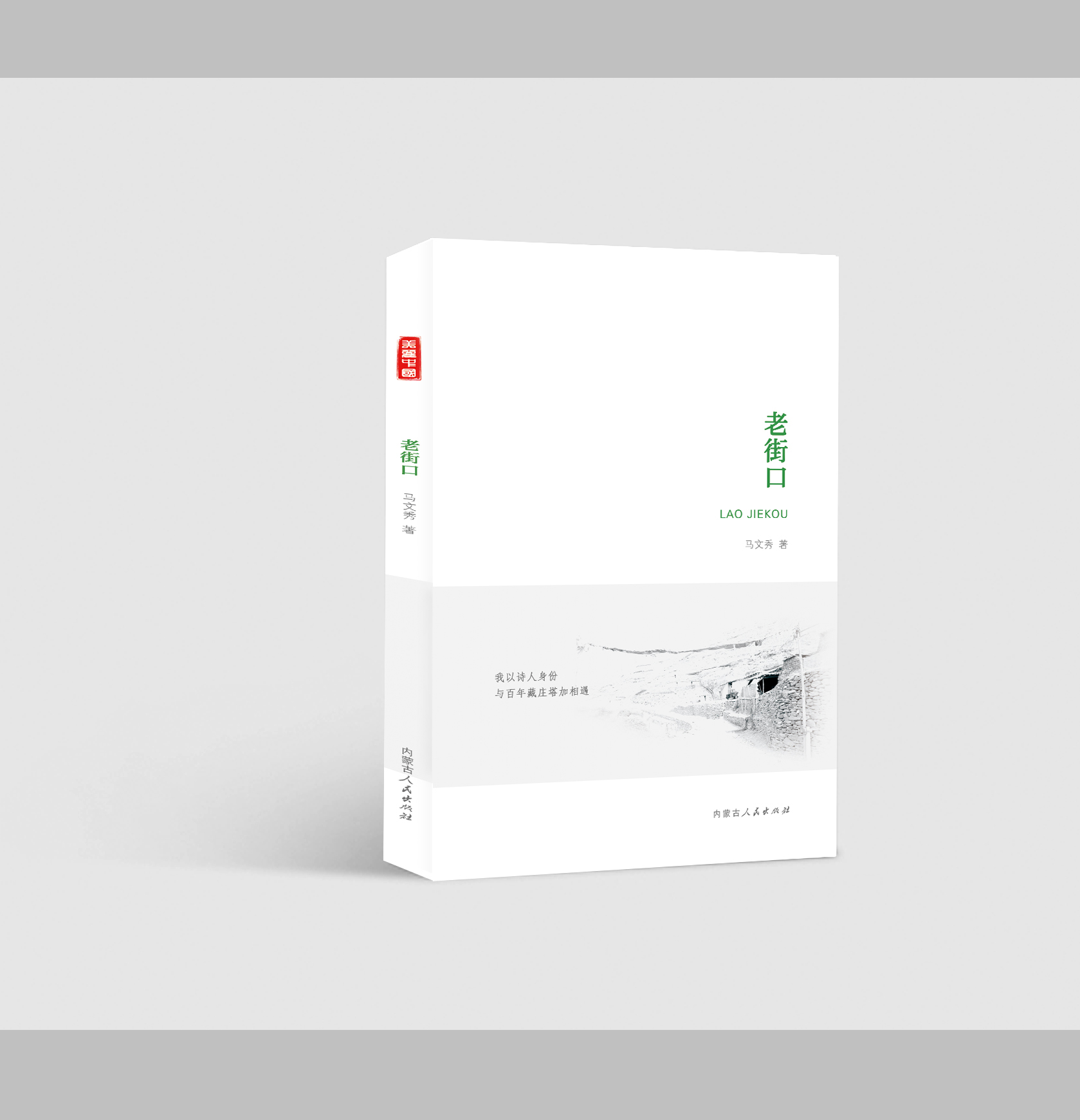
跺一跺脚,一个村寨就诞生了。怒吼一声,一个藏族汉子的形象就栩栩如生。一部诗集的诞生,犹如一盏酥油灯照亮了我们失落的精神故乡。
马文秀的每一句诗字里行间迸发出一股力量,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豪情万丈。青年诗人马文秀的文字里,藏着青藏高原的风与火——风是溪流与鸟鸣的私语,火是血脉与信仰的奔涌。她以女性写作者特有的细腻与力量,在诗集《老街口》中为塔加编织了一首跨越时空的童谣,让每个读诗的人,都能循着文字的辙印,成为这片土地的“诗中人”。
一、文字为舟:渡向心灵的原乡
马文秀的笔触是一把温柔的藏刀,将塔加的日常雕琢成诗。她写“溪流声、鸟鸣声、诵经声、嬉闹声争相组成惊喜的诗句”,让百年藏庄的光阴在声音的涟漪中复活;她将细碎的生活经验与遥远的亲切感打碎重组,融入读者的视听与味觉——你能看见石阶上被磨得发亮的岁月,听见土墙白石灰带在风中的低吟,甚至嗅到松木老屋中沉淀的光阴气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叙事,让塔加不再是地图上的偏远村寨,而是每个人心中隐秘的怀乡之所。
她擅于把一些琐碎的日常经验,一种遥远的而又亲切的感觉,打碎、调和到每一位读者的视觉、听觉乃至味觉之中,自然呈现出一种疏离与守望,把每一位读者自然地引诱到一种浓浓地怀乡之情中,用一种柔美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文字无穷尽的力量。同时,也让每一位读者不免对这片心灵深处净土的宿命感到隐隐地担忧。她运用最熟悉、最日常的事物引导万千读者涉足塔加,也是对塔加这片故土的深情告白。让每一位读者跟着她的足迹做一个性情中人,以诗中人的身份拉进与这篇土地的联系,运用诗歌欲言又止的表达方式,升华了每一位思乡者无尽的感怀,使塔加这片圣洁之地无形中成为千千万万读者向往的诗和远方。
她的文字更藏着对现代文明的隐忧。当物欲在都市蒸腾,塔加这片“白云深处的百年藏庄”,以700余年的古朴风貌成为时光的琥珀。她小心翼翼地触摸这片土地的过往与今生,像守护一颗脆弱的星子——怕它被文明的洪流冲淡,怕原始的信仰在喧嚣中褪色,这种深情的凝视,让每一位读者沉醉于诗意的缅怀中。
二、时光褶皱:藏庄里的千年密码
踏入塔加,便是踏入一部立体的民族史书。据载,这里的先民或是明朝中期驱驼迁徙的后藏部落,或是修建夏琼寺后留驻的永靖木匠,700年光阴在土木结构的老屋上留下印记:二楼住人、一楼畜圈的格局,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屋顶天井如一方凝固的天空,将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与藏民的信仰一同收纳。从山顶俯瞰,扇形环山的村落如大地的褶皱,每一道肌理都镌刻着游牧与农耕的交融。
巷道里,斑驳石阶诉说着世代足迹,白石灰带在土墙上蜿蜒如云端的图腾。这里的人们将对神山的崇拜、对祖先的敬畏融入生活——阿米尤合郎山与阿米康家神山的传说,保卫战的热血,文成公主途经的马蹄声,都在岁月中酿成了信仰的酒。马文秀的诗句便是开坛的引子,让历史的醇香在字里行间流淌,让每个“诗中人”都能触摸到藏民族血脉的搏动。这种双向的渗透,使塔加的每一块石板、每一缕经幡都成为文化基因的显性表达,而诗人的情感与思考,则沉淀为可触摸的物象密码。
来化隆如果不去塔加,只能说你对化隆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与“塔加”来一次亲密地接触,你就会对化隆这个盘踞青藏高原河湟谷底的小县城有不一样的理解。塔加,是一片被人类文明遗忘的最后的故土,它的存在,会让每一位去拜访它的游客时时担心有一天她会从地球悄悄地消失,它孱弱的存在会让每一位游客产生怜惜之情,生怕它有一天会被人类文明摧毁殆尽。
诗人与我,无疑也成为了一位怜惜之人,她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笔触,一句一词的试着去探索它的过往、今生以及来世。让世人通过吟诵去再次触摸这块世间最后的净土,以品读诗歌的方式唤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三、诗与远方:在文字中完成自我觉醒
塔加的珍贵,在于它是“被人类文明忘记的最后故土”。当我们在都市的钢筋森林中迷失,马文秀的文字为我们推开一扇木门——门后是松木的清香,是经幡的猎猎,是与天地对话的纯粹。她不是简单描绘风景,而是搭建了一座桥梁,让读者在诗中完成一次自我观照:在半农半牧的生活节奏里,看见对物质的淡泊;在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中,照见对欲望的反思。
在塔加村子的巷道里,农户门口错落有致的散布着斑驳、残缺不堪的石阶,石阶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被磨得光滑而又平整,似乎透露出整个村子的年龄,站在巷子口,我们依稀可见一代又一代的塔加子民,踩着石板路,背着背篓穿梭在巷子里的场景。巷子的土墙上被人为的喷洒着带状的白石灰,它们呈半弧形随意地挂在粗粝的墙体上,像图腾,又像散落在人间的丝丝白云,悠悠的散发着一种宗教气息和信仰观念。
走在这样的巷子里,一种古旧的年代感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当地藏民族对宇宙万物和大自然独有的理解和敬畏。他们追求与整个世界的一种永无止境的联系和解脱,把个人信仰与对祖先的崇拜、宗教的虔诚合为一体,完成着一次对生命最深刻而又无意识的体验,这种相互没有欺骗、没有敷衍的生活、生产方式造就了当地民众几乎与世无争、与世隔离的生存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这一点在马文秀的诗句里随处可见,这也让我们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还有作者的写作目的有了更清楚地认识。
马文秀以独到的目光,透视高原的神秘,探视当地藏族居民深刻的生命观和历史观。通过细腻的笔触,以诗会人,以诗化人,运用诗歌动人的音节,独特的意象,在读者眼前缓缓地打开了一张沉睡百年的地图。让读者以全新的视觉去了解、去关注塔加古村落,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具有鲜明化隆地域特色的心灵圣地,唤醒每一位读者向往的情感,激起主动去探寻这片神秘百年藏庄的欲望。
她以一名探访者的身份,对“百年藏庄”塔加村进行了一次深入地探索,立足“街口”,从“街口”往里走,探索塔加村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原始性与神秘性。从“街口”往外走,探索塔加村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这或许就是诗歌的力量:让遥远的塔加成为心灵的镜像,让每个“诗中人”在文字中穿越时空,既为古村的壮美惊叹,也为自身的生存状态沉思。当我们合上诗集,塔加的阳光仍在视网膜上跳跃,藏庄的故事仍在耳畔回响——原来所谓“诗和远方”,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心灵能否抵达的纯粹之境。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第五届中国长诗奖得主,马文秀的《老街口》以罕见的史诗性格局,在青藏高原的褶皱里展开了一幅关于藏民族生存密码的诗性图谱。这部由《探秘百年藏庄》《迁徙:祖先预留给勇者的勋章》《白云深处的百年藏庄》《塔加:青海古村落》构成的松散诗学建筑,看似随物赋形,却在现代诗的自由韵律中牢牢锚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原乡,让自然地理的塔加与诗性心灵的塔加在文字中完成了跨时空的叠影。
四、史诗结构:在断裂处重建文明记忆
马文秀的创作目的首先体现在对宏大历史题材的诗性转化上。她摒弃了传统民族志的线性叙事,转而以现代诗的跳跃性思维,将塔加700年的迁徙史、建筑史、信仰史编织成多维度的立体文本。第一章《迁徙》如同一曲苍凉的牧歌,用“一场迁徙,立于青藏高原/讲述雄浑壮阔的天地之美/他们穿越山川河谷/一路前行”这样的意象,将明朝中期后藏部落的东迁历程转化为可触摸的诗性符号;第二章对藏庄建筑的凝视,则化作“雕刻讲究的门扇、门枕石及两侧石墙角像颤巍巍的老人/守候在栅栏旁/以一株菊的安详/等待落日来临”的视觉诗学,让土木结构的老屋成为凝固的民族志。这种将历史具象化为感官体验的写法,使抽象的文明进程获得了体温与呼吸。
诗人对“形散神不散”的诗学把握尤为精妙。看似零散的章节实则暗含着精神的螺旋上升:从序诗的探秘视角切入,历经迁徙的史诗追溯、藏庄的空间解码,最终在第四章升华为对古村落现代命运的哲思。这种结构暗合着藏族文化中“轮回-重生”的宇宙观,让整部诗集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精神闭环——正如塔加民居的天井将天空纳入生活,马文秀的诗笔将历史星空纳入当下的精神场域。
五、心灵考古:在诗性凝视中完成精神返乡
当我们跟随诗人的笔触走进“白云深处的百年藏庄”,会发现《老街口》早已超越了地域书写的层面,成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根性的心灵考古。马文秀对塔加“半农半牧”生存状态的书写,实则是对工业文明的隐性反思:“挖掘机推倒老房子/乡愁瞬间从心底跌落/隔着高原的肌肤/能清晰感知落地的沉痛/数不清的泪水随之扑来/迎来无尽的遗憾/一刻比一刻冰冷”,这种与自然共生的智慧,恰似照进现代性困境的一束强光。她笔下的藏族汉子“跺一跺脚震落雪山的积雪”,不仅是族群形象的塑造,更是对人类原始生命力的礼赞。
这部诗集的精神价值,更在于其对民族文学的范式突破。马文秀没有陷入“文化猎奇”的窠臼,而是以主体自觉的姿态,将个人经验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当她书写“一座庄廓一条根/根下埋着祖先的遗训”“晒太阳的老妇/斜靠在夕阳的肩膀上/两眼微闭/静听风中夹杂的喧嚣”,既是对祖先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精神返乡的指引。这种“诗性之思”的开拓,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路径——让传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流淌在现代诗行中的活的文明。
合卷之际,塔加的星空似乎仍在头顶闪烁,藏庄的松木气息仍萦绕鼻端。马文秀用诗笔完成的,不仅是对一个古村落的文学建档,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情守护。当我们在她的诗句里看见“老房子脚下连着故土/每寸土地写满守候”“我与他席地而坐/一杯酒敬山下的路”,看见的其实是每个现代人失落的精神故乡。《老街口》的价值,正在于它让遥远的塔加成为可抵达的心灵原乡——在这里,历史不是故事堆里的符号,而是活着的传统;诗歌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文明的基因链。
进而让我明白,马文秀写塔加,是对故土的深情告白,更是对每个现代人的温柔呼唤。在她的笔下,塔加不仅是青藏高原东缘的古老藏庄,更是一种精神原乡的象征。读《老街口》,如同饮下一杯青稞酒,初尝是文字的甘冽,细品是岁月的醇厚,最后化作胸口的温热——让我们终于懂得,所谓“诗中人”,从来不是旁观者,而是带着敬畏与热爱,走进土地、走进自己的寻梦者。
来塔加吧,不必跨越万水千山,在塔加做一个性情的“诗中人”:让灵魂在松木的纹路里栖息,让心在经幡的光影中苏醒——这或许,就是马文秀藏在诗句里的,最动人的秘密。
很赞哦! ()


